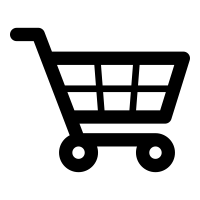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原创天地) 4832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1
今年,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50周年(1966年)和结束40周年(1976年),因此我一定要在今年把此文完成,以了却一桩长久的心事。其实早有写“我的文革记忆”的想法,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说法,那说法是“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我认为,文革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那真不一定,历史上有多少杀人无数的阶段尤其是战争阶段只不过距今人太远而已被遗忘(举个据今不太远的例子,如“扬州十日”,清军在16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的10天中就屠杀了扬州军民共计80万人,之后的嘉定三屠又杀了10万人。可现在的中国人有几人还知道“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呢),但文革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才过去四、五十年,但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文革已没有任何概念了。说抗日战争他们知道,说解放战争(或中立点说三年内战)他们多少也知道,但你问文革是什么他们则一脸的茫然。文革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中国人不是爱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可是如果没人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等文革一代人都死了,文革的真相就彻底消失了,还如何成为后事之师。第二个原因是,最近我突然发现记忆力开始衰退了,以前很熟悉的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以前很清晰的事情,突然就回忆不出细节了。这很危险,我这才想得赶紧动笔,否则很多人名就想不起来了。如果人名没有了,那回忆就失去了一多半的价值。所以我的这篇回忆,文采是次要的,首要原则必须是绝对真实,真实到记录的全是真名实姓的真人真事(想不起来的人名就说明想不起来,而绝不胡编一个名字),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1966年,我11岁,就被“卷”入那荒唐的文革岁月中了。
我头一次听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竟是在法语课上。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上学,学的是法语。我们的法语老师叫孟庆苏,是一个说法语比说汉语还流利的印尼归国华侨。那时我们的法语刚学了两年,每天又只有一节法语课,所以用法语还说不了什么复杂的事情。但孟老师经常鼓励我们用法语说话,出了错误他再纠正。那是1966年的春天,有一天上法语课,孟老师又说:谁用法语给我们说点什么?我们的法语小班长邸玉华就站起来了,她说:Hier mon père et ma mère ont dit que,…que…que (昨天我爸爸妈妈说….说….),她卡在那儿半天说不下去,孟老师有点急了(他是个急性子)就说:好了,你想说什么,用汉语说吧。邸玉华说:昨天我爸爸妈妈说现在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用法语该怎么说。当时孟老师脸色不是很好看,他显然并不喜欢这个话题。但他还是告诉我们了,他说:文化大革命用法语说是la grande révolution culturelle。这是我头一回听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除感觉很新鲜以外,心想这是谁编出来这么一个词,把很温柔的文化和很暴力的革命居然给绑到一起了。当时我还觉得挺纳闷,我怎么没听到谁说过这个词,也没见街上或是哪儿有什么文化大革命呀。
但后来,我们就慢慢感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气息了。首先是课堂上文化大革命的成分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的法语课。有一堂课我记得很清楚,孟老师要教我们用法语说“毛主席万岁”。孟老师问我们:你们知道“毛主席万岁”用法语怎么说吗?我们当然不知道。孟老师就告诉我们,“毛主席万岁”用法语说是Vive le président Mao。我们跟着他念了几遍就记住了。孟老师又问我们: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该怎么说呢?有同学说:Vive le président Mao,vive vive!孟老师说不对。又有同学说:Vive vive le président Mao!孟老师还说不对。我们东拼西猜,孟老师都说不对。我们就说不知道,快告诉我们吧。孟老师说:正确的说法是Vive le président Mao,qu’il vive longtemps très longtemps! 我的妈呀,这万万岁和万岁,汉语只差一个字,这法语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呀,这让我们猜三天也猜不出来呀。但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长长的法文版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Vive le président Mao,qu’il vive longtemps très longtemps!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个著名的口号,叫“破四旧,立四新”(文革语汇)。四旧是哪四旧,四新是哪四新,我始终也说不全,我感觉就是把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积累下来的那些传统的东西都归入四旧,都要打破,把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做法也要打破,或者改变。首先改变的是我们不住校了,变成走读了。文化大革命前,我上的这个北京外国语学校可是有点贵族学校的味呢。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部学生都是住校。我们小学部的三个年级,每个班不但有各门课的老师,还有一个生活老师呢。我们班的生活老师姓金,是个有点严厉的女老师。我记得每天晚上上完晚自习,我们都得排成队向宿舍走去。从这时起,我们就归金老师管了。她会监督我们刷牙洗脸洗脚,挨着屋子查看是不是都按时熄灯了,熄灯后是不是还有人在小声说话。我们每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第二天星期天的下午,就必须再返回学校。我们吃饭是在大礼堂,八个孩子围一张方桌,每个桌边坐两个人。菜是每人一份,等你坐上桌时面前就已经摆好了一盘菜,是炊事员事先给盛好的。主食是随便吃的。这种贵族生活我过了两年,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贵族生活先被破掉了,我们再不能住校了,改成走读了。我们学校的学生本来是从全北京市的所有学校中通过三轮考试拔尖子选上来的,因此有些学生家住在东城,有些住在西山,都离学校远着呢。原来每星期跑一次,住得远点也还受得了。现在每天放学回家,住得远的同学得倒几次车,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呢。幸亏我家离学校还不太远,我每天走着去,出计委大院北门,沿月坛北街向西走一站到钓鱼台国宾馆东门,拐向北走一站到甘家口,再往西走一站(这一站是郊区车的一站,比较远),一共三站到学校,还算是近的。
第二个变化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国老师就都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小学部每个班的外语老师都是两个,一个中国老师,一个外国老师。孟老师是我们的中国法语老师,我们的外国法语老师是个海地胖太太,我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管称呼她Madame(太太)。每班配外国老师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学到地道的外语。Madame一句汉语也不会讲,她上课就是硬讲法语,再就是用手势用实物来努力使我们明白她在讲什么。上课时,不到万不得已,孟老师也不讲汉语。Madame上法语课,孟老师就像个搬运工,Madame讲什么他就拿什么或搬什么。这堂课讲吃的,孟老师就抱来一堆盒子,有饼干,有糖,有水果。Madame一边讲还一边吃,有时候也让我们吃,她说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某一种食品是什么味道,其实我们早都知道。如果是讲大扫除,孟老师就扛着墩布笤帚,手提着水桶跟在Madame后面走进教室。有时候他一个人拿不了,还得再叫一个同学帮助他拿东西。
Madame走了,孟老师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从一个严厉到极端的老师变成了一个没一点脾气的老师,因为开始批判“师道尊严”(文革语汇)了。本来,孟老师是个在全校都出了名的厉害老师。白天Madame上课时,孟老师不会当着Madame的面发脾气,我们的早自习和晚自习都是法语课,那时候就只有孟老师,那就是他发威的时刻。他利害到什么程度?一根竹教鞭在他手里从来超不过一星期,几天就被他摔断了。你要惹他生气了,他不会拿教鞭打你,但会抡着教鞭使劲往你课桌上摔打,劲头大到几次教鞭就打劈了或断了。再或者,你如果惹他暴怒了,他不敢明目张胆地打你,但会揪着你的衣服领子把你提起来再按下去,就这么提起来按下去非来个十下八下才罢休,这一招比打你也差不多。一开始批判“师道尊严”,孟老师就变了,他不但再不发脾气了,而且态度还出奇地好了。不过孟老师倒不是被批斗吓的,而是他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错了。他是个头脑特别简单的人,从印尼回国就是因为觉得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既然现在毛主席说师道尊严是错的,他就真心认为自己以前是做了错事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怕孟老师了。
日常生活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变化就是过去安全、秩序和和谐的生活都消失了。
先说安全。文化大革命前,那时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全。文化大革命前三、五年的事我还有清晰的印象。那时我家住在计委大院的124门4号。那时的门锁很简单,就是门把手上随带的门锁,从门把手下面的钥匙眼把一个长把钥匙插进去向右转半圈门就开了。这钥匙没有后来的钥匙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高低不同的齿,因此这把钥匙不但能开我家的大门,还能开里面各个房间的门。更奇特的是我家还有一把钥匙,我们把它叫万能钥匙。它的把手比别的钥匙大很多,不但能开我家的各道门,还能开邻居家的门。因为住对门3号的那家,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进不去门了,就会到我们家来借万能钥匙。我现在想,这把钥匙应该是可以开124门全部6户人家的门的。但是,那时没有谁会觉得我们家有这把万能钥匙对他们有什么不安全的。那时,我们家晚上睡觉就经常不锁门。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可对睡觉不锁门这事有特别清楚的印象。因为我那时比较胆小,晚上不锁门我就害怕,不是怕小偷(那时我脑子里还没有小偷的概念呢),而是怕鬼或者什么黑衣人之类的半夜进来。睡觉前我经常问我父亲:锁门了没有?我父亲大概是为了锻炼我的胆量,我越说要锁门他越不锁门。有一次我实在闹得不行,不锁门我就不睡觉,他就把我家那杆气枪立在大门边上,说,这样行了吧。我那时还小,好哄,一杆气枪立在那儿让我放心多了,不锁门我也可以安心睡觉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安全就不存在了。从门锁的演变就可以看出。先是那个拿钥匙一捅门就开的锁谁也不放心了,都换了钥匙上有齿的保险锁了。再后来,普通保险锁已经不够安全了,门锁越来越保险和复杂,当然也越来越贵得出奇。再后来,光是门锁已经防不住小偷了,门锁周围要加钢板了。再后来,大家都知道,必须安装防盗门防盗窗了。我家那把万能钥匙虽然没有用了,但我还像宝贝一样保存着,因为我觉得它很神奇。但时间长了,又搬了几次家,那把钥匙还是彻底丢了。那时城市里安全,农村更安全。1965年暑假我回了一趟老家(我姥爷姥姥家),在河北省任县。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天,忘了因为什么事家里人都出去了,只剩我和二舅在家。后来,我们也得出去。出了大门,二舅拿一把挂锁套着门环把门锁上,然后很自然地一抬手,把钥匙放在了门框的顶上。我很好奇,问:为什么不拿上钥匙而是放门框上呢?二舅说:就这一把钥匙,咱们拿走你姥爷姥姥回来就进不了门了。现在他们回来了一看门锁了,就上门框上摸钥匙去了。我说:那不怕小偷也来摸钥匙?二舅说:没事,家家都是这样的。当时我想,这应该就是民风淳厚的具体写照吧。(注:这种锁门法我本以为今生再看不到了,没想到多年以后又见过一次,那是1991年在挪威。我当时因翻译的原因在原著作者霍伊姆教授家住了三个月。有一天,我们俩最后离家出门,霍伊姆教授做了和我二舅完全一样的动作,他锁上门,然后很自然地把钥匙放在了门框的顶上。那次我没有问为什么,我只是在心中感叹,在国内普遍安装防盗门防盗窗的今天,挪威仍然是一个民风淳厚的国家。)
完整帖子:
- 我的文革记忆 - 别样人生, 2017-04-18
![打开整个主题 [*]](themes/web_2.0/images/complete_thread.png)
- 以前从不明白文革。出国后慢慢看过很多回忆录和相关资料才有所了解。 - 我为诗歌狂, 2017-04-18
- 这个有意思。等空下来慢慢看:)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7-04-18
- 丽桥游子, 2017-04-18
- 喜欢看这样的纪实文字,今天有点空,看看能追到第几篇哈:)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丽桥游子, 2017-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