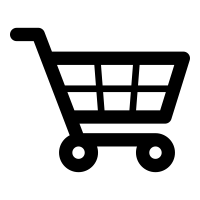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4 (原创天地) 5449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这一仗还真没躲过去。有一天就来了另一拨红卫兵,叫我们“燎战”退出中古友谊小学,由他们来占领。我们当然不答应,双方就打了起来。他们躲在学校大门两侧的围墙后面,只要从大门处一露头,我们就扔砖头,他们就赶快再躲到围墙后面。他们也往楼上扔砖头,把教室的玻璃全打碎了。不但我们这间教室的玻璃都打碎了,因为他们扔得不准,连两侧教室和二楼教室的玻璃也打碎了不少。双方你来我往打了一、两个钟头,他们始终攻不进校门。当然,我们也被封锁在学校里出不去。后来他们就在下面喊话:要求停战,他们派人上来谈判。我们同意,让他们派两个头头上来,其他人不许进校门,否则我们就把谈判代表绑了当人质。然后我们双方就在教室里开始谈判。那时兴大联合,立场差不多的红卫兵组织都联合起来以求人多势众。我们也是谈联合,那就看双方立场差别大不大。因为双方都是半大孩子,谁也说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说干脆也别打了,两个组织联合,共同占领中古友谊小学。谈判中间出了个插曲,差点使谈判破裂。本来双方已基本谈妥可以联合了,结果他们一个人又问了何小舵一个问题: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何小舵一愣,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就说:你们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于是就叫他们等,我们到另一间教室里商量。何小舵问我们:他们问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呀?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信仰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这个东西挺高大的,不能瞎答一个让对方低看了我们。结果有一个同学就说,他哥哥是中学的红卫兵,那天听他们说到什么“红胡子闹革命”,咱们就说咱们信仰“红胡子闹革命”行不行。何小舵想了想,说,我看行,咱们就算是信仰“红胡子闹革命”吧。然后我们又返回去,告诉他们我们信仰“红胡子闹革命”,你们如果同意我们的信仰,咱们就可以联合了。这回轮到他们发愣了。他们说他们也要商量商量,于是俩人就退到房角处低声嘀咕。我们那时很紧张,不知道我们这个“红胡子闹革命”会引发什么结果。过了片刻,他们回来了,说,我们同意你们的信仰“红胡子闹革命”,我们同意和“燎战”联合。我当时心里觉得很好笑,就这么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红胡子闹革命”,他们居然还就同意了。于是我们就联合了,他们那个组织叫什么我忘了,反正从那天开始只有他们的人和我们“燎战”的人可以进中古友谊小学,其他人进来我们都要盘问,看他们是干什么的。如果是闹革命的目的,比如押着他们的老师来开批斗会,那是可以进来的。我们也是红卫兵啊,当然要支持革命行动的。那时隔三差五就会有一群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进校来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老师们挨几个耳光那是太家常便饭的事了,我还看到过把写大字报的一整桶墨汁从老师头上倒下来的情景,和听说在批斗女校长白智时,红卫兵们在她头上钉满了图钉的事。更厉害的我没有亲眼见到,但厉害的后果我是看到了。有一天,我院的一个同学说前两天从中古友谊小学校园内那个高烟囱上有一个人跳下来自杀了。因为是两天以前的事了,所以这一次我没有看到那个人的尸体。又过了两天,消息就得到证实了,跳烟囱自杀的人是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我和赵谦光老师不熟悉,因为我在中古友谊小学只上了两年,但对赵老师还是有印象的,因为他是教导主任,每个新学期开全校大会时他都会出现在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个子很高,非常显眼。我不知道他受了什么样的毒打和污辱,但一定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否则一个人不可能轻易走上绝路。事后我到那个烟囱那去看了,烟囱一切如常,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只是烟囱侧壁上那一溜铁梯子的下面几层被密密麻麻地缠了很多铁丝网,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再有人爬上烟囱自杀。这个烟囱我们以前经常爬,胆子大的同学敢一直爬到烟囱顶,像我一般爬到烟囱半截就不敢再向上爬了。当时我想,现在即使没有这些铁丝网,这烟囱今后我也不敢再爬了,这个烟囱曾经是我们的玩耍之地,我以前看它觉得它像玩伴一样亲切,现在它竟成了杀人之地,现在看见它只让我感到恐怖。
我们要时刻防着别的组织来“夺权”,因此还要备战,随时准备反击可能的进攻。那时因为停课了,因此所有的课桌椅都集中堆放在几间教室里,于是那几间教室就成了我们的练兵场。我们把桌椅摆成复杂的地道,在里面钻来钻去,练习着“巷战”和“地道战”。由于“地道”里很黑,有时候我们还用扫帚报纸等自制火把照亮。有一天晚上,可能是谁的火把没有完全踩灭,结果半夜着了大火。因为都是木质桌椅,着起来火势很大,一连来了四辆消防车才把大火扑灭。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看了,几间教室被烟熏得漆黑,几百套桌椅焚烧殆尽。幸亏教学楼是砖砌的,消防车又来得及时,否则可能整座楼都烧毁了。那时候公检法系统基本上都瘫痪了,火扑灭了就算了,根本没有什么机构来调查一下这火是什么原因烧起来的,更没有什么追究责任和赔偿之类的事。自那天火灾以后,为了维修教学楼,学校大门被一把大铁锁锁上了,谁也不让进了,我们“燎战”也失去了这个阵地。
不久,也许是“燎战”还有了些名气,居然还有人来“抢班夺权”(文革语汇)了。那时候权就是那枚刻着“星火燎原战斗兵团”的印章,印章在何小舵手里,他就是“燎战”的司令。如果谁逼迫何小舵交出印章,他出示了这枚印章,我们就得认他为“燎战”的新司令。就好像古代那些江湖组织例如丐帮一样,谁举着那根祖传的打狗棍,谁就是丐帮的帮主。为了印章不被抢走,那些日子何小舵有家也不敢回了,怕被人晚上堵在家里。他整天东躲西藏,连我们也很少能见到他了。那时已经是1966年冬天了,他偷偷来一区时都是穿件军大衣,戴棉军帽,再戴个大口罩把脸捂的严严的。他时刻背一个军挎(即军用书包),里面就装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宝贝印章,用红绸子包着,再就是一把菜刀,用报纸包着。后来,何小舵来的越来越少,我们去三区找了几次也找不到他。再后来,何小舵就彻底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是跑了还是死了。随着何小舵的消失,因为印章没有了,“燎战”也就无疾而终了,我的短暂的红卫兵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我不再是红卫兵了,但大街上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了,因为从1966年8月到10月份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起,就开始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文革独特现象)。当然,说是全国大串连,其实主要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因为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更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而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北京啊,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呢。那时,亲眼见到毛主席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如果谁在见到毛主席时再幸福地和毛主席握了手了,那这只手可就不得了了,从此舍不得洗了,而且会有多少人来握握这只手,就好像握到了毛主席的手那么幸福。毛主席头两次接见红卫兵都是在天安门,那我没法参加,因为那都是有组织的。但后面几次都是毛主席坐在敞篷车里绕着北京城转着接见排在马路两边的红卫兵们,这我们就可以参加了。忘了是第几次了,接见线路中就有我家附近的钓鱼台路,我们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提前几个小时我们就赶到钓鱼台路,站在大批大批的红卫兵人堆里。那天等了足足有几个小时,最后有人喊:毛主席来了!人群就乱了,都往前挤,那阵势能挤死人。我个子小,周围的人都比我高,我什么也看不见。最后等我挣扎着挤到前边时,毛主席的敞篷车早就开过去了,我什么也没看见!虽然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我都没看见毛主席一面,但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毛主席给宋彬彬改名字的事。宋彬彬是宋任穷的女儿。宋任穷那是绝对的高干,因为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他就是上将了,而全军一共才只有55个上将啊。所以,宋彬彬是绝对的高干子女,因此她才能上天安门城楼,她才能有幸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权,平民子弟是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肯定认识宋任穷,那是从红军时代就跟着他闹革命的老部下,但他不可能连老部下的孩子也能叫上名字。宋彬彬回答道:我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哪个彬啊?宋彬彬回答: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就说了:文质彬彬不好,要伍嘛。从天安门城楼上一下来,宋彬彬立刻就改名为宋要伍了。这在当时,由毛主席赐名,这就相当于古代由皇上赐名一样荣耀。因为有毛主席亲自赐名,宋要伍后来可出名了,她成了当时北京红卫兵甚至全国红卫兵的象征性人物,连她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也成了很有名的红卫兵组织。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宋要伍他们肯定是更积极地闹起了革命,因为不久以后一个消息就传遍了北京,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批斗该校走资派时把校长卞仲耘给打死了。
因为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文革特有现象)的支持,那时对串联的红卫兵真是优待啊,坐火车都不用买票。你只要是戴着红卫兵袖章,说是去进行革命大串连(文革语汇),行了,火车随便上,随便去哪里都不用买票。不但不用买车票,到餐车吃饭也不要钱。因为红卫兵们是在干革命,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谁也不敢得罪他们,你敢不给他们吃饭,他们完全可以说你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那就可以当场开你的批斗会,甚至把你活活打死。那会儿的人也实在,不是红卫兵的人也不会冒充红卫兵去占那个便宜,或者说不敢冒充红卫兵。
红卫兵们不但坐火车不要钱,到了北京后吃住也不要钱。从北京火车站一出来,站前广场上就有红卫兵接待站,有人负责把红卫兵送到各个招待所去。最后,各招待所都住满了,就送到各个大学去,学校腾出学生宿舍给外地来的红卫兵们住。再后来,各大学也住满了,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真会想办法,通知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也要设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解决一部分红卫兵的住宿和吃饭问题。就这样,计委也接回来几百名红卫兵。计委接回来怎么办呢,也有办法,通知机关干部自愿去领人,根据你家的住宿情况,想领几个就领几个。我跟着我母亲去领过两回人。第一次领人是去的计委食堂。到那里一看,大食堂里人都满了,全是各地来的红卫兵。第一次我们领了五个红卫兵,我现在也记不得他们来自哪个省了。我们家一共就两间屋,全家挤进大屋,把小屋腾给这五个红卫兵住。那五个红卫兵是一个地方来的,五个人还是有男有女。那会儿反正也是革命时期,或者叫非常时期,大家睡觉反正也不脱衣服,而且都一心想着革命,谁也不去想男女之间的事,好像那时候人们的性别也都很模糊了,所以男女住在一起也绝不会出事。那几个红卫兵很奇怪,他们除了到吃饭时间就到计委食堂去吃饭以外,基本上不出门。而且他们整天把小屋的门关得严严的,也没什么响动,所以我总是很好奇他们在屋里干什么。有几次我找个借口(比如送水什么的)推开小屋的门,发现他们都是挤在那一张大床上坐着。我进去他们也不说话,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我,好像在用眼神问我为什么进来。每次弄得我也很尴尬,后来我就不再去看他们干什么了。因为能往家里领红卫兵,我父亲就给我姑姑写信,说如果她的三个孩子来北京串联,就去国家计委,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领回我们家住。我姑姑的女儿韩小征1948年生的,大儿子韩三平1953年生的,小儿子西林1954年生的,那时都正是红卫兵年龄。不久以后,他们还真来了。这一次我和我母亲是去计委大楼接的,在几百个红卫兵中费了点劲才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领回家。我记得领回家的不光是他们姐弟三人,还有两个他们的同学。照例,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小屋。他们到底都是高干子弟,又来自大城市成都,见过世面,所以和上拨红卫兵大不一样。上一拨那几个人是成天不出门,而我表哥表姐他们几个是成天不沾家。每天一早就出去了,说是到各大学去串连去了,不到晚上都不回来。晚上回来跟我们聊上几句天就都困得打哈欠了,然后就都钻到小屋睡觉去了。他们在我们家大概住了有一、两个星期,然后就回成都了。一拨拨红卫兵串联来了北京,一分钱不花就能乘火车,在北京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在闹革命的同时还能把北京玩个遍,这样的好事在过去是没有人敢想的。等他们回去,在当地传经送宝(文革语汇)这么一宣传,那必定鼓动起更多红卫兵的串联热情,于是更多的红卫兵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一批接一批地涌入北京。到了1966年底,恐怕国家也受不了了,国库再有多少财力也经不住成百万上千万人这么消耗,于是在1966年年底和1967年年初,中央又连续两次下发通知,停止大串联,撤销所有的红卫兵接待站。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大串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到半年时间就销声匿迹了。
1966年的下半年到1967年的上半年,那段时间是最混乱的。混乱到什么程度,混乱到任何人都有可能第一天还是打别人的人,第二天就成为被别人打的人;混乱到头一天这个人还是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第二天就成为戴高帽子坐飞机(批斗时的一种姿势,两人从后面把被批斗的人的胳膊使劲向上掰,第三个人揪着被批斗的人的头发使劲向上拉,)的被批斗对象;混乱到不管多高级别的领导人(全国只毛泽东一人除外)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平安,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牛鬼蛇神”(文革语汇)。那时候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太多了,开始还是全名全姓地说,例如说打倒吴晗、邓拓、廖沫沙,后来都嫌累赘了,喊口号也太长了不容易喊得整齐,干脆只提姓都不说名了,不熟悉国家领导机构的人都不知道打倒的是谁,也只管跟着乱喊。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着这些人名,这可能也是我从小学外语的童子功吧。(此处补充一句:打倒可不是解除你的领导职务那么简单,解除之后就是无休止的批斗,逼迫你承认各种罪名。这些老共产党人受得了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但受不了自己人的冤枉,特别是有些既是共产党又是知识分子的人,他们更看重自身的名节和清白,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就只有自杀以证清白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被打倒的吴晗、邓拓、廖沫沙,都既是共产党又是知识分子。邓拓是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社社长,于1966年自杀。吴晗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于1969年自杀。三人中只有廖沫沙,官职没另两位高,学问没另两位大,因此可能知识分子的脆弱性少一点,挺了过来,后来活到八十以上而善终。)
这些都是当时人们整天喊的口号:
打倒刘邓陶!刘是刘少奇,中国的国家主席呀,头一天还站在毛主席身边一同检阅红卫兵呢,第二天居然莫名其妙就被打倒了(当然也不能说是莫名其妙,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盾直指刘少奇,于是刘少奇立刻就被打倒了。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国的一号领导人用造反派贴大字报的形式打倒了中国的二号领导人),从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一变而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文革语汇),再后来干脆就给活活整死了,死的时候连真名也不能用,火化单上填的名字叫刘卫黄,职业是无业人员,不明底细的人看到这个名字和这个职业,准以为就是火化了一个盲流呢;邓是邓小平,没错,就是毛泽东之后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在文革初期,他是排在刘少奇之后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以后被送到江西的一个拖拉机厂当钳工,因为据说他年轻时参加共产党之前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就是钳工,这次是让他干回老本行;陶是陶铸,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打倒以后他被押送到安徽囚禁,他在那里被诊断患了癌症,但中央不批准进行手术,于是死在了安徽,死后也不允许他的家属去料理后事。
打倒杨余傅!杨是杨成武,解放军高级将领,副总参谋长;余是余立金,解放军高级将领,空军政委;傅是傅崇碧,解放军高级将领,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被打倒了,说明当时军队也已经被卷进了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中。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三支两军”(文革语汇),三支就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是军管和军训。既然有支左,解放军当然也要选一个左派组织来支持。如果这个左派组织不幸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了,但是支持它的解放军不能倒(解放军这面旗帜永远不能倒),那就只好把它的首长抛出来打倒喽。
打倒彭罗陆杨!彭是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罗是罗瑞卿,解放军高级将领,当时是总参谋长,被打倒又被批斗,他不堪忍受,跳楼自杀,没死,摔断了一条腿。摔断了腿造反派也不放过他,用一个大筐把他抬到批斗现场继续批斗;陆是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部长;杨是杨尚昆,解放军高级将领,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打倒王关戚!王是王力,关是关锋,这两个人头一天还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打别人的人,第二天就成了革命的对象;戚是戚本禹,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主要起草人,也就是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前边打倒彭罗陆杨的会议他是参与者之一,结果把彭罗陆杨打倒没多久就轮到他自己被打倒了。
有一阵子,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三个人之外,所有文革前的国家领导人都被打倒了。现在想想真是荒唐,如果这些人都是坏人,都是反革命分子,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中都是在一群坏人领导下的吗。但当时没人这么想,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代表毛主席的,他们说打倒谁那就是毛主席要打倒谁,毛主席说是坏人的那一定就是坏人。
那时政治人物上台下台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几天又被赶下台。
那时候文化艺术界受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写书的写历史,唱戏的唱历史,而那时历史是最容易被归入四旧的。那时,人们不时听到某一个人们熟悉的文化人甚至艺术家又自杀了,在从1966年到1968年短短的两年内,这样的人名可以列出一串:
著名作家,“茶馆”、“四世同堂”和“骆驼祥子”等名剧的作者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吞安眠药自杀。自杀后被军代表命令开膛破肚,说要看一看有没有把搞特务活动的发报机藏在肚子里。那时候,这样荒唐的理由都有人信,或者即便不信也不敢不执行军代表的命令。开膛时把严凤英的尸体脱光,赤条条陈在案上,军代表就站在跟前盯着看,说道:我虽然没有看过你演的戏,但今天我看到了你的原形;
著名翻译家傅雷竟是夫妻双双在同一天结伴上吊自杀。
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当时国家队的三个乒乓球运动员,因为球打得好当时被称为中国的“乒坛三杰”,尤其是容国团,是在庄则栋之前在第25届世乒乓赛上夺得男单世界冠军的中国乒坛第一个世界冠军。他们就是普通的运动员啊,而且都是才30多岁的年轻人,可在文革中,容国团被认定是国民党特务,傅其芳被认定是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姜永宁被认定是日本汉奸,三人竟于1968年4至6月在短短三个月中相继上吊自杀。
那时有多少文化人自杀谁也没统计过,就我耳熟的文化名人在文革中自杀的起码还能写出下列:上官云珠、杨朔、言慧珠、小白玉霜、关露、赵惠琛、翦伯赞、顾而已、范长江、周瘦鹃、顾圣婴、罗广斌、舒绣文、李广田。在一个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年代,能有那么密集的文化人自杀现象,仅这一个现象就可以证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时期。
(注: 这些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些人名而已,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可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甚至如雷贯耳的名字呢。上官云珠是著名电影演员,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那个时期最著名的电影;杨朔是著名作家、散文家,他的作品收在小学和中学的课本里;言慧珠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小白玉霜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评剧中的白派艺术就是因她而命名的;关露是作家,也是个传奇的红色特工,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足可以编一部电视剧;赵惠琛是著名话剧演员;翦伯赞是著名历史学家,而且在当时被喻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翦伯赞也是夫妻双双自杀,他死后人们从他口袋里找到两张纸,一张纸写着: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另一张纸居然写的是:毛主席万岁;顾而已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范长江是著名记者;周瘦鹃是著名作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顾圣婴是著名女钢琴家,她是在批斗会上惨遭批斗者扇耳光的羞辱之后和母亲及弟弟三人开煤气自杀的;罗广斌是著名作家,红色小说《红岩》的作者,那本书在当时家喻户晓,里面的人物如江姐、许云峰等都是那时青年人的心中偶像;舒绣文是著名电影演员,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那时中国电影界有个四大名旦之说,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人是秦怡、白杨、和张瑞芳)。李广田是著名散文作家,曾出版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电影《阿诗玛》即是根据该诗改编拍摄的。)
完整帖子:
- 我的文革记忆 4 - 别样人生, 2017-04-19
![打开整个主题 [*]](themes/web_2.0/images/complete_thread.png)
- 电影界的名人的事情记得后来读到过。一直觉得上官云珠这个名字真好听。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电影界的名人的事情记得后来读到过。一直觉得上官云珠这个名字真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