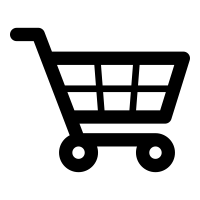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5 (原创天地) 5434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砸烂公检法”,“百万雄狮”,“火烧英国代办处”, 光听听这些名词也可以想象出那段时间国家已经处于多么不正常的状态了。
一月风暴是指1967年1月份发生在上海的造反派夺权行动。上海当时势力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叫“工总司”,在他们的司令王洪文带领下工总司的工人们冲进了上海市委,抓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当场就宣布他们不再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了,而是走资派和反革命了,直接就押往批判会会场去批斗了。然后造反派们就效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成立了一个上海公社,由它来代替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成了一群工人来管理上海这座人口上千万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的造反夺权行动居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而且还给他们提了个建议,说为了避免人们以为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里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呢,建议他们把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各省的造反派群起效仿上海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纷纷夺了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时每隔几天或几个星期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就登出来了,哪个省的革命委员会又成立了,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9月全国所有的省都成立了省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当年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就叫“祖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
1967年1月有上海的“一月风暴”,2月份就是北京的“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本来就是国务院的一次普通的讨论工作的会议,结果在会议上以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老资格元帅们为代表的不赞成造反派夺权的所谓右派和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为代表的支持造反派夺权的所谓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说谭震林气得拍了桌子,因使劲太大把手都拍骨折了。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支持了左派,于是老帅们的行为就被定性为反对文革的“二月逆流”,陈毅等五个副总理和徐向前等四个军委副主席全部被打到,从此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再无人敢反对的最疯狂阶段。
“砸烂公检法”可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当年还真有公安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三家联合给中央的报告,请求大幅度裁撤公安和法院工作人员,把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交给人们群众去监督改造。就这样的报告中央也批准了,导致公安局派出所除了搞运动什么案子也不管。
武汉当时有两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和“百万雄狮”,各自都有几十万人,百万雄狮的人数更是多达120万人。这样两个造反派组织相互对立,最后发展成武斗,先用铁棍等冷兵器,最后发展到动枪动炮,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大城市中有两支人数上百万的武装力量开枪开炮地对打,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大国发生过这样的事?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的。据说在香港闹革命的红卫兵被港英当局抓了,于是在北京上万名红卫兵围住了英国代办处,要他们放人道歉。在围了几天后,最后围堵演变成进攻,在8月份的某一天晚上,红卫兵们分三路冲破了由解放军战士守卫的英国代办处的围墙,把英国代办处的办公室砸了,把院长里的英国外交牌照的车全烧了,还把躲进地下室的英国代办用烟熏的办法逼了出来,打了个头破血流还把他摁倒在毛主席像前跪着请罪(那时的红卫兵倒是一点也不崇洋媚外)。此事闹到周恩来不得不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道歉,并全额赔偿英国代办处的财产损失。
下面这些事都发生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而且都发生在我的身边。
有一天,我母亲拿了一把锯,在家里锯她的高跟鞋的高跟(其实顶多算是半高跟)。她说,这鞋还好着呢,可是不能穿了,大街上见穿高跟鞋的就给你扒掉,说不定还打你呢。可是扔了又太可惜,把高跟锯掉了还能穿。本来,她有几身漂亮的旗袍,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再也没有穿过旗袍了。
我们小学部的同学没有红卫兵组织,停课闹革命就回家了,而中学部的学哥学姐们正可以全心全意地闹革命了。校长莫平被打倒了,党委书记程壁被打倒了,教导主任姚淑禧也被打倒了。他们都遭受了我们学校中学部的红卫兵的毒打和折磨,而且一定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毒打和折磨。因为,校长莫平和教导主任姚淑禧都自杀了。姚淑禧1966年8月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厕所里的水管上上吊自杀,据说她那一天遭到前后五拨红卫兵的毒打,实在挺不下去了。姚淑禧一个江南女子,长得文静清秀,说话慢条斯理,可红卫兵打她还不算,还对她百般凌辱。他们把她剃了阴阳头,还把从厕所里找来的厕纸篓扣在她的头上。我们班的女同学钱德超亲眼看到了那一幕,她写到:那个厕纸篓是金属丝编的,当时就有尖锐的金属丝划破了姚主任的脸,鲜血顺着她的脸流下来。姚淑禧在留下的遗书中写到:我实在受不了了。校长莫平个子不高,偏偏我校两个副校长雷力和张树勋都是大个子,开大会时他们一起站在台上时更显得他矮小,再加上戴一副白边眼镜,我们这个莫平校长从外表看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他从1966年被打倒,到1968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不断被批斗和折磨的境地。(注: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程壁也被打倒了,她也受到了毒打和折磨,但她没有自杀,挺过了文革。多年后在回忆文革遭遇时她这样写到:我和莫平等人被关进学生宿舍楼一层东侧一间装有铁栏窗的屋子里。在被关的日子里,对我们实行了残酷的专政,每天上下午几个学生轮流到屋里来对我们训话,训话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通拳打脚踢,动不动就打嘴巴,打得我们皮青肉紫。有时用脚踢我们,直到把人踢得倒在地上才罢休。我们几个人每天早晚都要轮番挨打,莫平被打得最厉害。后来,每次听到打人者的训斥吼叫声,都会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1968年5月,莫平听说又一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语汇)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一定是预感到这次他肯定要被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了(他是地主出身),于是在一个晚上跑到北京郊外的十三陵,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莫平也留下了一封短短的遗书,其中写到:我不理解,我想不通,我不反党。莫平和姚淑禧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而且都有地下党的经历,应该说他们都不是那么脆弱的人,当年地下工作那么严酷的环境他们都熬过来了,却熬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疯狂。那时我们北京外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北京市都出了名了,因为打死或斗死了几个走资派,说明他们的革命性多么强。而且,他们打死的还不仅仅是走资派,居然还把我校一个普通的女校工刘桂兰也给打死了,而刘桂兰只有一个罪名,就是她被查出是地主出身。我校中学部的红卫兵们(他们也不过就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在批斗刘桂兰时对她进行了毒打,使用的工具有铜头皮带和铸铁自来水管,还有练习拼刺用的木枪,最后竟当场把她活活给打死了,就在我们平时吃饭和开会的那个大礼堂的门口。当时,她的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她还是个处在哺乳期的妈妈。至此,我认识的人中已有五个人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非正常死亡(李梅跳楼自杀,莫平和姚淑禧上吊自杀,刘桂兰被棍棒打死,赵谦光跳烟囱自杀)。
有一天在三里河三区的44中学,一派红卫兵把另一派红卫兵的一个头目给抓住了。那个红卫兵头目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叫董维宁。红卫兵们把董维宁押进一间大教室,说是要开他的批斗会。我跟我们院的孩子也去看热闹,我们也都挤进了教室。开始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懂,反正是红卫兵们说他不老实,于是就开始用皮带抽他。那时因为都停课了,所以教室的课桌和座椅都是在教室的前部摞起来像山一样,这是为了腾出地方开批斗会和组织大的活动。董维宁被打得受不了了,他就往那摞着的课桌的高处爬,他爬上去用皮带就抽不着他了。红卫兵们就出去找了很多砖头回来。有人就扔砖头砸他,因为距离很近,这些砖头都准确地砸到他的头上和身上,几分钟之后他就已经头破血流了,又过了没两分钟他就失去知觉从上面跌下来了。那天估计因为都是一个学校的还算手下留情,这派红卫兵一看人已经昏迷了,批斗也不能继续进行了,就扔下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董维宁撤退了。
有一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甚至还参与了一个抄家行动。我家住165门2号,抄家发生在隔壁166门2号。2号那一家我不太熟,因为第一,那家孩子的父母都不是计委的;第二,他家的孩子都比我要小,最大的女孩顶多上一、二年级,她的两个弟弟更小,还是学龄前儿童呢。虽然不熟,但因为离得太近,可以说是从大人到孩子,我们是天天见面。那家男人动手能力很强,成天自己鼓捣一些东西。那时候自行车很难买,要有自行车票,否则你有钱也不卖给你。有一个星期天,那家男人在后院摊开一大张油布,然后从家里一趟一趟搬出很多自行车零件,从车架到车轮子到各种零碎什么都有。我们很好奇,立刻围了上去。那男人说,买自行车要票,买自行车零件可不要票,他陆陆续续把自行车零件都买齐了,今天他要撺出一辆自行车来。我们都很惊讶,也很佩服,自行车在我们眼里那是多么复杂的一个机器呀,它只可能是在工厂里靠众多的工人和设备才能生产出来,谁见过个人能撺出一辆自行车来的。我们围成一圈,看他撺自行车。撺自行车肯定不是简单事,他也是一会儿装,一会儿拆,一会儿装不下去了就在那皱眉头。就那么装了几乎一天,到下午他终于把自行车装成了。我们对他那是从心眼里佩服。从那天起,那男人每天都是骑着他那辆组装自行车去上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兴起了一阵打鸡血,说是把大公鸡的血输进人的身体,能强身健体,百病不侵。那家男人就信了,正好他家也有一只大白公鸡,他就经常提着大公鸡到医院去打鸡血。因为男人动手能力强,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是走资派,因为走资派都是领导,是不可能也根本没那本事自己动手撺辆自行车的。那家的女人更是看着就像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下妇女。可是,那一天,抄家就发生在他们家。
那天一大早,来了一群人,说是那男人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来了。男人不在家,说是已经被关在单位里几天都没回家了。造反派们把女人和一女两男三个孩子集中在院子里,然后就进入他们家开始抄家。我们都挤在后院他家的后门处,那时叫“围观”。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是:一个造反派用双手很费劲地搬着一个大鱼缸走了出来。鱼缸里是假山水草,和五颜六色的金鱼。他走到那家的女人和孩子面前,再使把力把鱼缸高高举起,然后,使劲往地上一摔。鱼缸粉碎了,满地都是水和在地上翻腾的金鱼。女人不敢吭声,孩子们吓得直哆嗦。那个造反派很得意地转回身,又继续进去翻腾去了。那家我去过,他们家既没有像样的家具,而且从他们家孩子的穿着看,也不像是有钱的样儿。我们好奇的是从他们家能抄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来。过了一会儿,抄家的造反派们出来了,看样子他们也很失望,没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围在那商量了一会儿,就走过来。他们把三个孩子关在他们家那间小一点的屋子里。在院子里,他们围成一圈,把女人围在中间,就开始批斗。批斗就是叫她交代问题,交代他男人的罪行。我也听不懂要她交代什么问题,估计那女人也不知道要她交代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她说不知道,造反派就说她态度恶劣,就冲着她使劲喊口号,还有人上去扇她耳光。突然,那女人就紧闭双眼瘫倒在地上了。造反派们一看她昏迷了,就开始抢救。有压胸的,有拍脸的,可是她就是不睁眼。这时一个挺粗壮的女造反派说,来,让我来。她用左手托着女人的后脑勺,右手使劲地掐那女人鼻子下的人中穴。她是用指甲掐的,因此很快就掐出血了。这时那女人哼了一声,把眼睛睁开了。他们一看她醒了,就把她提起来站着,继续批斗。其实当时连我都看出来了,那女人是实在不知道要她交待什么,就想装个死,心想我昏倒了你们就不能再批斗我了吧。谁知那女造反派更狠,拼命掐她的人中穴,人中穴是很疼的穴位,那女人疼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再假装被抢救醒了,宁肯继续挨批斗也不敢再装死了。这时有造反派来说在他家里发现一个地洞,所有的人都来了精神。我们也纳闷,这是五几年苏联帮助建设的宿舍楼,地面都是厚实的水泥地面,这要能挖出地洞来那反革命或特务那就坐实了。造反派们都涌进他们家,我们也跟着挤进去看。我一看就明白了,哪是什么地洞,就是供暖管道的出口。计委宿舍是集中供暖,而且是水暖,因此在楼房的下面有长长的地道。这地道的高度可容一个人半蹲着行走,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出口。我们家就有一个出口,出口平时是用一块两尺见方半尺多厚足有百八十斤重的水泥板盖着的。正好他们家也有这么一个出口,造反派就说发现地洞了。造反派把水泥板掀开,就派了几个人打着手电下去了。过一会儿那几个人上来了,说没搜到什么。从早上折腾到中午,造反派们准备撤退了。走的时候他们把那家的女人也带走了,说到单位继续批斗去。他们把三个孩子锁在小房间里,还让我们这些院子里的半大孩子帮他们“监视”这几个孩子。那天他们家大门后门全都敞开,任人出入。我们还真就认真地执行造反派留下的任务,过一会儿就去“监视”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活动。屋门是锁着的,但门上面有一扇活动窗,是玻璃的,站在一把椅子上就可以从活动窗看到屋里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那女孩说他弟弟想看书,我们就商量,说可以给他们看书,但是只能看革命的书。我们就在他家里翻找,最后就把一本毛主席语录从门上的活动窗给他们递进去了。想想看,她弟弟可是个还不认字的学龄前儿童啊。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怕抄家,一是父母官都不大,算不上走资派;二是我们这个家是解放(1949年)后才成立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能算得上四旧的东西。但那些有点儿解放前家底的人家是真怕呀,一旦有值钱的东西抄出来,那接下来就是批斗,伴随着的那就是打骂,弄不好打死了也是白死。因此,那时候很多人家就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收旧家具旧物件的商店(那时叫旧货商店),有些人家甚至连卖都不敢卖,怕被旧货商店的人揭发,因此都是趁黑夜把东西偷偷扔掉。扔也不敢扔在附近,比如扔在楼下的垃圾箱里,怕被人发现顺藤摸瓜找上门来。因此,那时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经常能“捡”到值钱的宝贝。
夏天,除了闹革命之外,我们打发时间最多的活动就是去玉渊潭钓鱼或游泳。有一天,我们几个男孩子又去玉渊潭游泳。到了东湖边,脱了衣服,我们就下水了。刚把脚伸进水里,我低头一看,浅水里有一个闪亮的东西,就弯腰伸手把它捞了起来。拿到手上我一看,原来是一个银元宝,和电影里看到的银元宝一模一样,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托在手心里沉甸甸的。我兴奋地喊了起来:嘿,看我捡到了什么!周围的人都围过来看,都说这肯定是谁家怕抄家夜里偷偷扔在湖里的。他不可能跑大老远只为扔一个银元宝,这水里一定还有别的。于是大家就四散开来,都弯着腰在水里摸。这一摸不要紧,还真捞上不少东西。最多的是银元,都是真正的银元,俗称袁大头的那种,因为银元上印着袁世凯的头像。有的人摸到一个,有的人摸到几个,就这一小片水域摸上来几十块银元。还有就是照片,都用布袋子装着。因为都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所以那些照片都快泡烂了,但还能看得出来,都是很老的歌星影星的照片,不用说,都是属于四旧的内容。我们正在浅水处摸呢,前边深水处一个男孩兴奋地喊了起来:我踩着个大家伙,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就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片刻之后他冒出头来,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瞪着眼,张着嘴,他手上居然举着一把长长的刀。我们簇拥着他上了岸,围成一圈研究这把刀。这把刀的形状我们太熟悉了,电影里,地道战里的鬼子龟田腰里挂着这样的刀,平原游击队里的鬼子松井腰里也挂着这样的刀,这是一把典型的日本指挥刀。刀长足有一米,重量足有三、四斤。从刀鞘里把刀往外一抽,明晃晃一点绣也没有。用手一试刀刃,奇怪,一点也不快。仔细一看,这把刀就没开刃。指挥刀为什么不开刃,一圈人谁也说不上是为什么。一看水里竟然有日本指挥刀,人们又转身往水里跑,都指望再捞上个什么稀罕玩意儿。但那天从捞上那把日本指挥刀以后,那片水域就再没捞上什么东西了。那时候人们觉悟都很高,而且又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谁也没有想把捞上的东西据为己有。大家商量的结果,都认为应该上交。交给谁呢,又是一阵商量,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上交到最近的派出所,月坛派出所。那天的月坛派出所很热闹,每交上一件东西,民警都要进行登记,然后还要给上交人写一张收据,因此把几个民警也忙活了半天。那天我也拿到了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上交银元宝一个”。
完整帖子:
- 我的文革记忆 5 - 别样人生, 2017-04-19
![打开整个主题 [*]](themes/web_2.0/images/complete_thread.png)
- 还写收据啊:)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还写收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