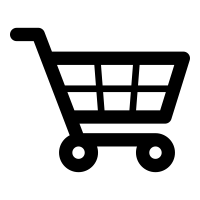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7 (原创天地) 4874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那时候,我们知识没学多少,倒是干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不是学生应该干的事。比如挖防空洞。那时人们互相防着互相打,连国家也像是患了多疑症,整天宣传说苏联要侵略中国,因此要“深挖洞,广积粮”(文革语汇)。深挖洞就是挖防空洞,苏联飞机来扔炸弹了好有地方躲。那时候北京市的各个单位都挖防空洞,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挖防空洞先得选地方,一般是要选一片开阔的地方,不知道是革委会还是工宣队(这都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机构)竟然选中了大礼堂旁边的桃园。本来那一片桃园里有上百棵桃树,春天时桃花盛开,蜂蝶飞舞,可算是我们学校中一个美丽的景致。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沾花沾草的那都是资产阶级坏习气,都在被打倒破除之列,这恐怕是选中桃园挖防空洞的革命理由。挖防空洞是个大工程,各班的学生都排了班,下课后轮流去挖防空洞。那时挖防空洞就是大开挖,像战争年代挖战壕一样,每个学生拿一把铁锨,挖一铁锨泥土然后使劲扔到壕沟的两边。挖了几天之后,那战壕就有一人深了,我们往上扔土也就越来越费劲了。有一天,忽然壕沟底下有人惊呼起来:死人!死人!挖防空洞挖到死人了,在壕沟里正挖土的同学都吓得面无血色,仓皇出逃。我们都跑到桃园去看,原来不知道是哪个同学,一铁锨下去,铲到一个圆鼓隆冬的东西,再一使劲,竟然挖出一个人头骷髅来,这还不吓死人了。后来才知道,几十年前,在建成外语学校之前,这里曾是一大片坟地,因此这地底下到处都是陈年尸骨。后来就越挖人骨头越多,吓得我们只敢在大白天才下去挖。后来防空洞是修好了,但从来也没用过。那时候全北京修了多少防空洞,全是白修,因为到底苏联飞机也没来轰炸。后来很多防空洞改建成了地下旅馆,算是找到利用地下防空洞的新用途了。如今北京有蚁族一说,就是说的住在由防空洞改建的地下旅馆中的人们,他们久居地下,像蚂蚁一样,因此被称作蚁族。
除了挖防空洞,为了准备打仗,我们还要接受其它的军事训练。最简单的训练是我们都学会了打背包。由军宣队的解放军战士给我们做示范,然后经过反复的练习,我们都能够用一根背包带子在一、两分钟之内把被子打成一个方方正正的背包。乱捆是不行的,背包带必须是“井”字形,大家的背包从外观上要“整齐划一”。不光是一条被子,在被子里面还要放置必要的用品,比如用换洗的衣服做成的枕头和毛巾牙刷牙膏等盥洗用具。打背包是最简单基本的军事训练,还有更复杂的,比如如何用步枪打飞机。我们被告知,如果美帝和苏修的飞机来轰炸了(那时也真厉害,中国是准备和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打仗的),解放军自然是要用高射机枪高射炮打的,但我们要“全民皆兵”,每个人用步枪也要对准天空,这才能叫敌机有来无回。军宣队的解放军战士在黑板上给我们讲解怎么样才能用步枪打下飞机。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是你不能瞄着飞机打,因为飞机是在几百上千米高的天上呢,而且还是快速向前移动,如果你瞄着飞机打,等你的子弹飞到飞机的高度,那飞机早跑到前面几百米的地方去了。那怎么打呢?你得用提前量打,即冲着飞机前面多少米的地方放一枪,等子弹飞到飞机的高度,飞机正好飞到这里碰上你的子弹,那么飞机就会被步枪打下来了。解放军战士告诉我们,步枪子弹打到机身上也可能打不透,但飞机的驾驶舱也是玻璃的呀,你要是碰巧把机舱玻璃打碎了,把飞行员打死了,那飞机不就掉下来了吗。理论上是不错,问题是这个提前量可不好计算,要考虑飞机的高度,还要考虑飞机的速度,这已经很复杂了吧,更要命的是不同的飞机的飞行速度是不同的,你还得先学会辨认是什么型号的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那速度可是差远了,于是这个提前量变成了复杂无比的问题。当然最后美帝的飞机也没来,苏修的飞机也没来,我们也始终没有机会验证用步枪能不能打下飞机。
再一个是学农劳动。到1968年,继红卫兵运动以后,毛主席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又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对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到1968年这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那时叫老三届),不像文革前的正常做法,毕业后在户口所在地的城市分配工作了,而是全部下到农村去当农民。当时当农民分两种,一种就是直接到农村去,到生产队里落户,叫做插队。另一种是到东北、新疆,或者云南等边疆省份,进入半军事化管理的成建制的生产建设兵团。据文革后的统计,当时全国上山下乡的城市户口毕业生共有2000多万。)我校中学部的学哥学姐们有去东北建设兵团的,也有去延安插队落户的。不但学生去,连老师也有去的,而且很多人还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的。我的法语老师孟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我前边说过,孟老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毛主席说的话都是对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一般都是从批判“师道尊严”开始的。从那一天开始,孟老师不但再不对学生发脾气了,他甚至改得都“矫枉过正”了,他不让学生们再叫他老师了。他说:我比你们也大不了多少岁(他应该比我们就大个八、九岁),以后你们不要叫我孟老师了,就叫我老孟吧。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孟老师就向学校要求和初中部的同学一块去陕北插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使孟老师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孟老师小时候那也应该是养尊处优的。他的父亲叫孟鞠如,解放前是民国政府的资深外交官,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驻各国的使馆工作。因为他是学法语的,因此曾长期担任中国驻法国的商务参赞。他的几个孩子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而且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生的。在哪个国家出生,孩子的名字中就带那个国名中的一个字。孟老师叫孟庆苏,那个苏字就是苏联,因为当时孟鞠如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孟老师因此出生在苏联。新中国成立前夕,孟鞠如干了一件大事,他率领民国政府驻法国使馆九名馆员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孟鞠如回了国,以后一直在外交学院教授法语。孟老师从苏联到印尼又回中国,虽然辗转多地,但从未真正吃过苦。现在,他竟然主动要求到生活最艰苦的陕北去当农民。而且,那时候人们去插队并不是临时打算,那是要转户口,要准备一辈子在那里当农民的。一个说汉语都不如说法语流利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竟准备一辈子当农民了。孟老师后来真去了陕北,他在那里插队劳动了整整三年时间,直到文革后期才被学校招回来继续当法语老师。那时我见到他时问他:你现在说汉语该比说法语流利了吧。他说是,现在说汉语是比说法语流利,但是看报纸还是觉得看法文版的人民日报比看汉文版的人民日报更容易。但是,从陕北回来后,孟老师就逐渐无法适应社会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的言谈已显示出他已经无法适应文革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了。他对我说:我现在不能出门,出门就生气,在单位看不得那种对上级阿谀奉承,对下级颐指气使的小人做派,在社会上看不得各种歪风邪气,尤其不能进商店买东西,我看不得售货员对顾客的恶劣态度,我肯定要和他们争吵,所以,现在我们家买东西都是我爱人去。(这里得补充一句,不然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顾客是上帝呀,售货员态度不好,如何卖得出去东西呢?文革时和现在可不一样,那时物资紧缺,人们买东西都像是求着售货员,而且那时商店都是国营的,售货员都是铁饭碗,因此那时的售货员高人一等,对顾客从无笑脸不说,还动不动就训斥顾客呢。)孟老师是那种性格特别直率的人,他看不惯的事情他是无法忍而不发的。忍不了售货员他可以不去买东西,都丢给他爱人,在单位你叫他如何忍呢。从此,他在哪个单位也待不长了。从陕北回来没两年,他就离开了外语学校,去了新华社。在新华社待了不到三年,他又离开新华社去了中建总公司,在那里当了几年法语翻译(其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国外,可虽然是在国外,但还是在中国的援外工程队伍中,因此他看不惯的人文环境并没有变化),等我几年后再到中建总公司去找他时,那儿的人说他几年前已经不在中建总公司了。至于他又去了哪里,没人能告诉我。从那次以后我就失去了孟老师的任何音讯。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孟老师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8年时我上初中一年级,还不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但我们也要学农,就是要经常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我们最常去的是四季青人民公社,一是因为近,走几里地就到;二是四季青人民公社当时是北京市在西郊树立的先进典型(文革语汇),他们也习惯了安排学校的学生来劳动。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四季青公社劳动,所以每个季节的农活都干过。我记得有一次是初冬,我们又去四季青公社劳动。到了地头一看,是一大片白菜地。所有的大白菜都被拔起来了,码放成一摞一摞的。我们站成两排,听生产队长给我们布置当天的劳动任务。生产队长是个老农民,满脸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张口就说:恁们今儿个这活茬儿呢……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离城里没多远的地方,他们说的话竟然是这样的。那天我们要干的农活就是把每一颗大白菜外面的枯黄的烂叶子撕掉,让它变成一棵干干净净的新白菜,然后装车运到城里的菜站去。那天的天气非常冷,一棵棵白菜就像一个个冰坨子,撕几分钟手就已经冰凉了。可是我们谁也不敢戴手套,因为社员们都没有戴手套,干着农活儿还戴手套那是小资产阶级习气,是不能吃苦的表现(文革语汇),那肯定会在劳动后的总结会上受批判的。我有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畅的毛病,到了冬天,即使身上不冷,手脚也是冰凉的。一到冬天,我手上脚上都要生冻疮,因此我冬天最怕用手碰凉的东西了。我当时心里想这是谁发明的大冬天赤手撕白菜叶这种活儿,好像是专门为了惩罚我而设计出来的。本来就生着冻疮的手,因为一整天都被这冰坨子一样的白菜冰着,冻疮就更严重了,两手肿得像馒头,都攥不成拳头了。最后肿得太厉害把皮肤都撑破了,从破口处往外流黄水,伤口一冬天都合不上,一直拖到第二年的夏天才完全愈合。从这以后,每年冬天我手上的冻疮都会复发流黄水,一直到成年以后才慢慢地好了。还有一次是在四季青公社的货场劳动,我们的任务是搬筐。货场东边像座山一样堆了几百上千个柳条筐,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筐从货场的东边搬到西边,还照样堆在那儿。那个货场没多大,从东边搬到西边也就是三、四十米的距离,当时我实在想不明白那些筐堆在东边和堆在西边有什么不同。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生产队长成天接待城里的学生来劳动,他哪有那么多活儿给你安排呀。可不给你安排又不行,学生们是来学农的,你还得支持啊。于是就给我们安排这么个活儿,把筐从东边搬到西边。说不定等我们走了,又一批学生又来了,生产队长就对他们说:恁们今儿个这活茬儿呢,是把这些筐从西边搬到东边。这样,就这一堆柳条筐,他就可以接待无数多的学生来学农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真是一个聪明的农民,把城里人都忽悠了。这倒真应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文革语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连载 9
除了这种小学农外,还有大学农呢,就是要到农村去住上一段时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和贫下中农们打成一片(文革语汇)。1968年的夏天,我们学校就组织了这么一次。那个农村就远了,是在顺义县的一个叫“陈各庄”的村子,那离北京市得有七、八十里远呢。我们是先坐汽车,出东直门一直向东北方向开,后来到离那个村子还有几十里的地方就停车了,全部学生都下了车。这时已经天黑了,校领导说,下面的路要徒步走着去,既学农还要拉练,两者一块进行了。拉练也是那时候发明的,就是背着背包长途徒步行军,也是为了打仗而准备的。那时候也真奇怪,好像随时准备要和苏联人打仗似的。于是大半夜的,我们这几百个中学生,背上都背着自己的被子,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漆黑的农村公路走了几十里路,到天亮才走到那个陈各庄。到村里后,我们被分到各家去住,每一户农民家安排四、五个学生。我和几个同学被领进一户人家,他们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住。进屋一看,靠前窗的一侧是一个大炕,两头顶山墙,和屋子一样宽。我们高兴极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睡过炕呢。谁知,我们住下的第一天晚上就出现意外情况了。晚上,我们并排躺在那大炕上,虽然劳动了一天挺累的,但是因为是第一天,什么都新鲜,我们就东聊西聊睡不着。躺了一会儿,我们发觉真的睡不着,这炕怎么这么热啊。拿手一摸,这炕真的是热的。这可奇怪了,此刻是大夏天,我们是来参加麦收的,总不会大夏天还给我们烧炕吧。于是我们就悄悄地下炕,悄悄开门,到屋外侦查一下这炕为什么是热的。我们发现外面有一个土灶,土灶后面就连着我们睡觉的房子。凑到灶眼前一摸一试,灶膛里还热得很,说明刚才这灶里还生过火。我们退回屋里,就开始分析,这家为什么要在大夏天烧炕。分析的结果让我们很兴奋:我们八成逮到了一个阶级敌人。贫下中农是不会大夏天烧炕来烫我们的,这家解放前一定是地主或者富农,所以他才会想出这种恶毒的手段,使我们在劳累了一天后也不能好好睡觉。当天晚上因为灶膛的火已熄灭,炕慢慢就不热了,我们后来还是都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了带队老师,让他联系生产队长,查一查这家人解放前是不是地主富农。带队老师相当重视我们说的情况,他让我们去正常劳动,他负责把这件事查清楚。当天收工回到村里后,老师就把我们屋的同学叫到一起,向我们宣布他今天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令我们有些失望,这家不是地主,而是正宗的贫农。他昨晚是用那个灶烧了一锅水,因为我们是第一天住在他家,他一时忘了屋里炕上还睡着几个城里来的学生呢。当然,从那天以后,他晚上就不再用那个灶烧水了,一场热炕风波就这么过去了。那两个星期我们是真正地和农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我亲眼看到,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将近二十年了,农民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让我尤其想不通的是,农民是种庄稼生产粮食的,可是农民却吃不饱饭。为了省粮食,农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起来不吃早饭,扛上农具先下地干活儿去了。到上午九点钟下地的男人回来吃第一顿饭。这顿饭没有干的,而是玉米面粥,干活儿的男人饭量大,玉米面粥用小脸盆盛着,喝满满的一盆。我问他们为什么光喝粥不吃干的,他们说是为了省粮食,说如果用同样多的玉米面做成窝头,只能做几个,还没吃就没了,而做成玉米面粥能喝一大盆。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心酸,这不成了种庄稼的没饭吃了,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啊。但那时候,这想法是不敢说出来的,说出来就成了对社会主义不满,那是要受批判的。
那三个星期中,劳动是辛苦的,但劳动之余的农村生活对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结识了一对农民兄弟,他们叫申学光和申学深,收了工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玩耍。他们兄弟俩教我怎么掏麻雀窝。麻雀窝都在房檐下,砖墙顶上靠屋檐处的一些小洞就是麻雀做窝的地方。但哪个洞里有麻雀哪个没有呢,你总不能见一个洞就搬梯子爬上去掏吧,那你掏十回得有八回是空的。窍门是你得观察,如果老麻雀进出很繁忙,那肯定是麻雀窝,老麻雀得不时地叼回虫子喂小麻雀。再就是你站在墙跟前仔细地听,如果有小麻雀你会听到头顶上传来微小的鸣叫声。有一次我不小心掏了个蝙蝠窝,吓得我差一点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来。当时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掏了一个麻雀窝,几只肉滚滚的小麻雀我已经掏了出来,小心地放在口袋里。我正准备下梯子,发现旁边还有一个洞,我想管它有没有,伸手掏掏又不费事。我把手伸进洞里,还真有一个毛绒绒的东西。我把它抓在手心里,把手从洞里退出来。我张开手一看,妈呀,哪是什么麻雀,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母蝙蝠,因为它的肚子上还有两只小蝙蝠,它们都紧紧咬着大蝙蝠的乳头,吊在母蝙蝠的肚子上。我生平最怕两种动物,蛇和老鼠。这蝙蝠那就是会飞的老鼠呀,所以我是把蝙蝠归在老鼠一类的。手里抓着个蝙蝠,当下吓得我“啊”了一声把蝙蝠赶紧甩了出去,那蝙蝠顺势就飞走了。我赶紧爬下梯子,从那天起我就再不敢随便掏麻雀窝了,因为这下我可知道了,那窝里不光有麻雀,还有蝙蝠呢,更可怕的是说不定还有蛇呢。
完整帖子:
- 我的文革记忆 7 - 别样人生, 2017-04-19
![打开整个主题 [*]](themes/web_2.0/images/complete_thread.png)
- 接受再教育了:)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接受再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