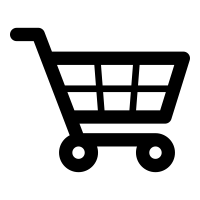我的文革记忆 9 (原创天地) 5056次阅读
观看【别样人生】的博客1969年5月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了,而这一次的最新指示竟影响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个指示叫五七指示(文革语汇),具体怎么说的谁也记不住,中心意思就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们都应该集中到设在农村的干部学校去进行劳动锻炼和接受思想改造。那时,执行毛主席指示真叫雷厉风行,马上,所有的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都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学校。因为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成立的干部学校,所以统称为五七干校。国家计委当然也要成立五七干校,在1969年的7、8月份就派人去选址。当时有两个地方计委可以选择,一个是贵州的花溪,一个是湖北的襄樊。花溪是离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仅50多里的一个小城市,据说是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襄樊的那个地址离襄樊市还有上百里远呢,而且是在比农村还偏远的地方,是没有农民居住的劳改农场。结果最后计委干校的校址被定在了襄樊。放着各方面条件好的花溪不去非要去更艰苦的襄樊,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叫做“宁左勿右”(文革语汇)。8月份选好了址,10月份就动身,而且是计委全体干部连同家属上千人要一同出京。那架势有点像古代哪个大臣犯了罪被皇上抄家了,全家老少加上佣人丫鬟上下几百口人被逐出京城发配远恶军州。不过说是全部也不确切,计委又不能关门,还是要留下少量的干部应付日常工作的。文革初期时计委干部也分成了两派,人多的一派叫造反公社,是反对计委主任余秋里的,因此也叫造反派。另一派人少,叫红委会,是保余秋里的,因此也叫保皇派。余秋里先被造反派打倒,后来又被中央保了下来继续当计委主任,从此造反公社的干部就都成为“站错队”的人了。这次去干校,造反公社的干部一锅端,全部得去干校,而留在计委继续工作的基本是红委会的干部。当时真有人撒泼打滚就不去的,宁肯受批判办学习班也不去,但大部分人是不管自愿或不自愿,都只能服从命令。而我则是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离开外语学校了。我并非不喜欢外语学校,那是我的荣耀,是曾经显示我的聪明的舞台;我并非不喜欢我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班的三个老师,那都是我的人生榜样。法语老师孟庆苏的性格清澈如水,单纯到如同婴孩,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种人性;语文老师张永亮一身正气,在他身上你永远看不到一丝的歪门邪气,他长得又黑,我总有种感觉他是古代的那个清官包公托生来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齐惠珍在表面的严肃下对学生有一颗像母亲一样的爱心,她对所有的同学都很好,但我却总感觉她对我有特殊的偏爱。当然,也许每个学生对自己喜爱的老师都会有这种感觉吧。我也并非不喜欢我的同学们,五年的同窗,前两年甚至是同吃同住,一天到晚厮混在一起,对他们的感觉甚至就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感觉。但那时,我只想离开外语学校,离开我的同学和老师,这个血统论,这个出身决定一切的政治环境对我的自尊心的打击太大了,我心里清楚,今后我再怎么努力也将无济于事,我当不了兵,入不了团,出不了国,所有的好事都没有我的份(这些后来都被我的经历所证明。比如出国,那时外交部要从我们学校选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作为外交人才储备,我们班有三个名额。挑选的第一标准不是看学习成绩而是看出身,只有贫下中农和工人出身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初选,接下来才看学习成绩什么的。而我,是连进入初选的资格都没有的。)。而且,我还得处处谨小慎微,别人敢骂的我不能骂,别人敢打的我不能打。那时在我眼里,我的未来是一片黑暗。而去五七干校,对别人可能是惩罚,而对我则是解脱。去干校的人,都是去接受改造的,谁也不会嫌谁黑了,谁也不会在意我的富农出身了。我当时有一种冲出牢笼,飞向自由的感觉。
计委一出动还真就不一般,专门包了一个火车专列。那列火车不卖票,所以车上没别的旅客,全是计委的干部和家属,足有上千人。虽说不卖票,但也不能乱上的,车厢是按计委的局划分好的,我母亲是综合局的,综合局的干部和家属都上8号车厢。一般一个车厢可以安排两个局,综合局是个大局,人多,一个8号车厢几乎叫综合局占满了,只有最后面的三、四排是另一个局的人。我们家是三个人,我母亲,我,还有我妹妹,她那年才12岁。我父亲那时已不在计委了,他调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已经去了西安,否则我们就是全家四口人全上计委干校了。我们的家具和大部分东西都留在北京的家里,三口人只带了两只木箱,和其他家的箱子一起装在后面挂的几节行李车里。行李车里不光有各家的箱子,还有几节行李车里装的都是家具,主要是床板,那不是各家的,而是为干校的集体生活准备的,因为到了干校起码得先有床板可以睡觉吧。那时毛主席出行他不爱坐专机,他就爱坐专列,而他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沿途所有的列车都得给他让路。而我们这列计委专列就没这个特权了,因为是列车时刻表之外另加的,因此得见缝插针,给正常的客货列车们让路,所以我们的这列车经常在一个车站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磨磨蹭蹭化了两天的时间才到武汉。然后掉头向北,又开了一夜才到了襄樊市。到了襄樊市,我们还得换乘大卡车继续走,而且这回是一家三口分别上了三辆卡车。我母亲上的是去计委五七干校的卡车,开往离襄樊市以北一百公里远一个叫太山庙的地方。我和我妹妹上的这两辆卡车过了太山庙还要再向北开,要一直开出湖北省,开到河南境内去。我那年上初一,初中的学生们去河南新野县的一个村子叫官渠,我妹妹他们这些上小学的孩子们要去的地方叫韩营,也在河南,但离我去的官渠还要再远三、四十里地呢。就这样,我们家三口人分散在两省三地,如果算上在西安的我父亲,那时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家是一家四口人分住在三省(湖北、河南、陕西)四地,彼此谁也见不着谁。
我当时和一百多初中年龄的同学们住在官渠的一所空着的农村学校里。简陋的教室就是我们的宿舍。没有床,只有地铺,而且分配铺位时是用一块砖头量尺寸的,每人只有一块半砖头的宽度,你的褥子只能对折着铺下去。晚上躺下去,人挨着人,一个人翻身,旁边人准醒,醒了也就趁机翻身,再旁边的人又醒了,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翻身,大家全醒,全都翻身。那房子是土坯房,简陋得四面透风。我们刚住进去没多久就到了冬天,湖北的冬天冷得很,还经常下雪。下雪时如果再刮风,那雪就会从四面八方的孔洞处飘进来。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一会儿,人就被凉醒了,因为落到脸上的雪被脸的温度溶化了,流到脖子里人就凉醒了。醒了拿手电一照,嘿,满屋子飘着雪花,被子上已积了薄薄一层雪。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下雪的时候我们都把雨伞撑开,遮住脸,这样起码脸上不落雪,可以继续睡觉。在屋子里打着雨伞睡觉,别人都没听说过的事我还真亲身经历了。
白天我们大部分时间上课,任课老师就是计委的干部。我们按年级编成班,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叫杨邦杰,他是计委基建局的干部,我父亲离开计委之前就在基建局,所以杨邦杰老师我以前就认识,以前叫杨叔叔,现在叫杨老师了。上课也没有课本,由着老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临时过渡性的,只是因为干校那边条件太差不得不先找个地方把这些孩子们安顿了。
除了上课,因为已经是在农村了,就是经常性地到四周的村子里去参加农业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两件事我还留有清晰的记忆。一次是到村里去吃忆苦饭(文革现象)。到了村里找到生产队长,带队老师说明来意,就是让孩子们吃顿忆苦饭,忆苦思甜(文革语汇)。于是队长就领着我们挨户转,到一户就留下几个学生,由这户给做一顿忆苦饭。中午全吃过忆苦饭了,下午回到学校就开会忆苦思甜。老师先让各组汇报都吃的是什么,结果吃什么的都有,好的有吃馒头的,差的有吃窝头的,还有吃红薯的(吃红薯对那时的北京孩子来说简直就是美食了),就是没有吃糠和吃野菜的。把老师气的,敢情生产队长没听懂吃忆苦饭的含义,以为就是把孩子们送到各家吃派饭呢。结果,那天的忆苦思甜没达到预期效果。
另一次是在一次抗旱劳动时,因为发生了一件笑死人的事所以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是1970年的春天,小麦该返青了,可是多少天不下雨,小麦开始大面积旱死。周围的村庄都在抗旱,于是我们也去帮助老乡们抗旱。我是第一次见到那样原始和无效的抗旱。男人提个桶,女人端个盆,小孩子也跟着,拿个碗或提个玻璃瓶子。每个人就用这些作容器,从池塘里舀上水,走几百米到麦地里,一次就浇那么三、两棵麦苗。我心说这能救得了麦苗吗?等把这几亩地浇到头,最前面浇的麦苗已经又要干死了。可是,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只能跟着干却不敢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我们学生连的盛水容器就整齐多了,就是每个人的脸盆。几个大个的男同学负责用大木桶从池塘里打上水来,倒进地上摆放的一片脸盆里,然后各人端起自己的脸盆,走上几百米,浇上几颗麦苗,然后再返身重复这个程序。突然,有一个男同学一失手,把木桶掉进了池塘里。少一个桶就降低了效率,再说这桶都是跟生产队借的还得还人家呢,所以这桶非得捞上来不可。那时是三月份,天还冷着呢,我们都还穿着毛衣毛裤呢,所以没人敢下水。一个初二的同学叫什么我忘了,因为他有点弱智,即便当时我们也都是叫他的外号“大傻”。大傻大喝一声“我下去!”于是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都注视着他,要看他的英雄壮举。直见大傻三下两下就把上身的衣服脱光成了光膀子,然后他就开始脱裤子。本来他是应该把外裤毛裤脱掉剩个裤衩的,肯定他也是这么想的,可谁知他把所有的裤子连裤衩一下褪到了脚髁处还不自知,结果就那样前面是鸡鸡后面是屁股地站在那里。女同学都惊得“哇”的一声尖叫,他这才发现赶紧弯腰把裤衩提了上来。结果惹得男同学们哈哈大笑,女同学们抿嘴窃笑,他自己羞了个大红脸。
那时候我母亲每两个月可以有一个星期天来看我和我妹妹一次。她来一次那可辛苦了,那一天她要骑自行车跑一百多里路,从湖北骑到河南。因为干校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很多,所以这样跑的家长也很多,那一天他们都是几十人结伴而行,人多相互可以有个照应,人多脑子多眼睛多,也可减少走错路的风险。我妈他们早上天不亮就出发,骑五十多里地赶到官渠看我。在我这儿呆上一个钟头,吃顿饭喘口气,然后再骑三十多里路赶到韩营看我妹妹。在那里照样呆不了多一会儿,就得赶快往回返,回到干校就快半夜了,第二天早上还得照常出工呢。我母亲他们来的那天,如果赶上下雨那他们就更艰难了。他们走的很多是乡村的土路,一下雨就变成烂泥路,根本骑不成自行车,那他们就只能推着自行车走,一推就是几十里。偏偏湖北的天气是冬天也下雨,而且好像故意和人作对似的,特别爱在星期天下雨,所以当时在干校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湖北天气怪,刮风下雨逢礼拜。礼拜就是礼拜天的简称。
过了大概有半年时间,干校那边条件稍微好一点了,可以安置孩子们了,于是官渠和韩营的点都撤销了,孩子们都回到自己父母所在的连队。那时计委干校的校部设在一个叫太山庙的小镇上,干校完全按照部队的编制,整个计委干校下设四个连队,分散在四个地方。最近的是我们二连,离太山庙有五、六里路。最远的是四连,在离太山庙三、四十里远的一条山沟里。二连应该是计委干校的主力连了,计委的几个大局像综合局、基建局、劳动工资局、重工局、轻工局的干部都编在二连,再加上家属和孩子,得有几百号人。连下面按计委的局再分成排,像我母亲所在的计委综合局的番号为二连二排。之所以说二连应该是计委干校的主力连可不仅仅是因为人多,还真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多。当时二连的连长是计委轻工局的副局长杨波,他后来在八十年代成为国家轻工业部的部长。二连的指导员叫姜巍,当时是综合局的普通年轻干部,后来海南建省那年他已经是国务院体改委改革试点司的司长,从中央空降到海南省担任了海南省第一任的经济计划厅厅长。二连的主力那又得说是我母亲所在的二排,说这个二排是藏龙卧虎之排或全中国五七干校第一排都不过分,因为除了姜巍外,综合局的副局长柳随年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当了中国的物资部部长,还有八十年代享誉中国经济界的经济学家杨启先、刘日新、陆百甫当时都是综合局的普通干部,因此那时也都在二连二排劳动。大关子得卖到最后,如果光是这几个人我也不敢吹嘘说二排是全中国五七干校第一排。敢吹这个牛是因为1998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并被中国人称为铁腕总理改革总理被外国人称为经济沙皇的朱镕基当时就在二排,因为他那时也是计委综合局的普通干部,而且因为是右派(即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定为右派),他那时在排里还是最老实巴交的。所以二连二排就这么三十几个人中就至少出了一个总理,一个部长,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而在当时,他们都是接受劳动改造的普通五七战士。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假如文革不是那么快结束而是继续下去,这些国家的栋梁之材还都在干校种地呢,朱镕基成不了总理,柳随年和杨波也当不上部长。幸好,历史没有假如。
二连除了这些按局编的劳动排之外,还有汽车班、饲养班、炊事班、木工班等。除了汽车班的司机就是原来在计委小车班给部长局长们开车的司机外,饲养班的饲养员、炊事班的炊事员、木工班的木匠们,那都是计委的干部,而且很可能级别还不低呢。例如,计委副主任贾庭三文革前就已经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了,而那时他就编在二连,而且是编在二连的饲养班里养牛。别人蹲牛棚那是个形象的说法,而他是名副其实地整天就在牛棚里伺候那一群牛。我偶然间发现牛棚里老鼠特别多,而且都是不算尾巴光身子就有半尺长的大老鼠。我前边说过,我对老鼠是又恨又怕,能在保证老鼠碰不到我的情况下杀死老鼠是我的最大快事。那几年,无论是在外语学校还是在干校,我的弹弓射鸟之准是没有对手的。在发现牛棚里老鼠特别多之后,我就发现用弹弓从远距离射杀老鼠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距离远不用担心老鼠会钻进我的裤腿,而且不管多大的老鼠中我一石弹都非死即伤。因此我闲了没事就爱到牛棚去用弹弓打老鼠。贾庭三很喜欢我去,不是因为我打老鼠,他不像我那么恨老鼠,而是我去了就有人和他说话了。因为牛棚就他一个人,连晚上他也是一个人住在牛棚里隔出的一个小间里,因此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个人可以和他说话。我一去,起码有个人可以说说话了。那时候,他可一点没有个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样子,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平常的老头儿,而且待人和善没什么架子。平时没人时,实在闷得慌了,他就和那些牛说话。他给那些牛都起了名字,像对人一样和那些牛说话。我喜欢看他喂牛,因为喂牛时他就和那些牛说话,说的还特别有意思。他会一边往料槽里加料一边和牛聊天说话,走到每一头牛跟前都跟它说上两句。比如添料添到一头大黄牛跟前了,他就说:大黄呀,你急什么,人人都有份,少不了你那一口,别总显得那么没出息。写到这里我脑海里马上想起另一个人来,他比贾庭三还要孤独。牛棚好歹就在二连驻地,贾庭三多少还能有个把人和他说说话,而那另一个人是十天半月都碰不上一个人和他说话的。那人叫陈裴章,是计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干部,专门给计委主任副主任们写发言稿的。因为文章写得好,号称计委一支笔。他的编制也在二连。连里把他派去放羊,那羊圈可不在二连驻地,而在离二连驻地十几里远的河滩上。一个大羊圈,一间小茅草房,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里。他只能每隔十天半月回连里来领一次给养,能见到人说说话,其余的日子他就是一个人守着一群羊。为了身边有个伴儿吧,他养了一条狗,那狗浑身雪白没一根杂毛,他给它取名叫小白。因为陈裴章整天就这小白和他做伴,他肯定也是把它当人看待了,几个月的功夫把小白调教得比人还聪明。除了一般的狗都会的把戏之外,最绝的是小白通音律,会跳舞。陈裴章多才多艺,除了会写文章,还会拉二胡。他只要一拉起二胡,小白马上闻声起舞,它立起上身,只用两后脚站着,围着陈裴章转,一边舞还一边叫,胡琴声不停它就一直跳一直叫。而且,曲子不同,你觉得它的叫声和舞步也有变化。那时我们都没见过会跳舞唱歌的狗,所有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小白肯定是哪个人托生来的。(后来小白死了,而它的死竟也是那么诡异。后来,连里把陈裴章调回了连里,派了另一个人去羊圈。小白肯定是要留在羊圈的,陈裴章不能回连里过集体生活了还把小白带在身边。从此小白就变了,它白天经常从羊圈跑回来,就在二连驻地附近四处转悠。而且它也没有了原来的精神,经常是找个地方就趴下睡觉,谁也不理。有一天,我们在二连附近的一块地里干活,在这块地和二连之间就是刚通车不久的焦枝铁路线。我们都看见,小白当时就趴在路基上睡觉。当然,像往常一样,也没人去打扰它。突然,远方一列火车开过来了。因为刚通车不久,火车还稀罕,另外也趁机停下歇歇,因此火车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火车。所有的人都看见,火车已经离得不远了,可是小白仍然趴在路基上睡觉,对火车巨大的轰鸣声毫无反应。有人就喊了起来:小白!小白!快下来!小白仍然一动不动。我们都急了,有几个人开始向铁路跑去,一边跑一边呼喊。突然,小白站了起来,但是它没有向路基外跑,在我们几十个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它竟然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路基上迎着火车头跑去,转瞬之间,它就被巨大的火车头吞没了。等火车开过去,我们都赶忙跑上路基。路基上只有小白的尸体,一个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为了怕陈裴章见了伤心,我们就在干活的地里挖了个坑把小白埋了。从那以后,谁再说见过一只狗有多聪明,听说过一只狗舍身救主,我都相信。)
完整帖子:
- 我的文革记忆 9 - 别样人生, 2017-04-19
![打开整个主题 [*]](themes/web_2.0/images/complete_thread.png)
- 花溪是很美啊,没选那个地方可惜了:)
![空帖子 / 没有文字 [ 没有文字 ]](themes/web_2.0/images/no_text.png)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丽桥游子, 2017-04-20
- 花溪是很美啊,没选那个地方可惜了:)